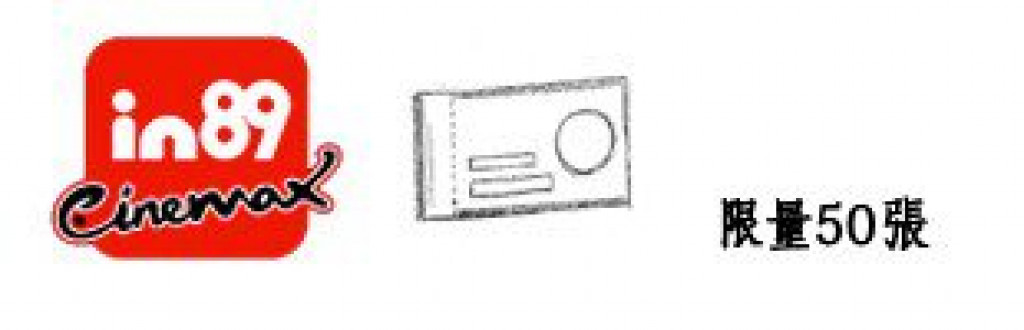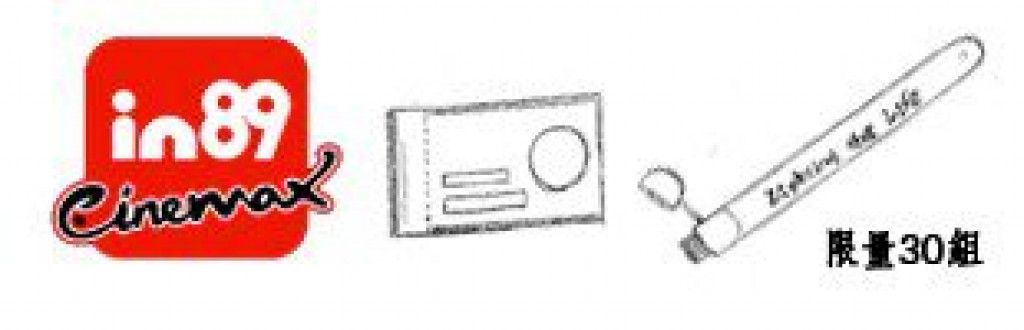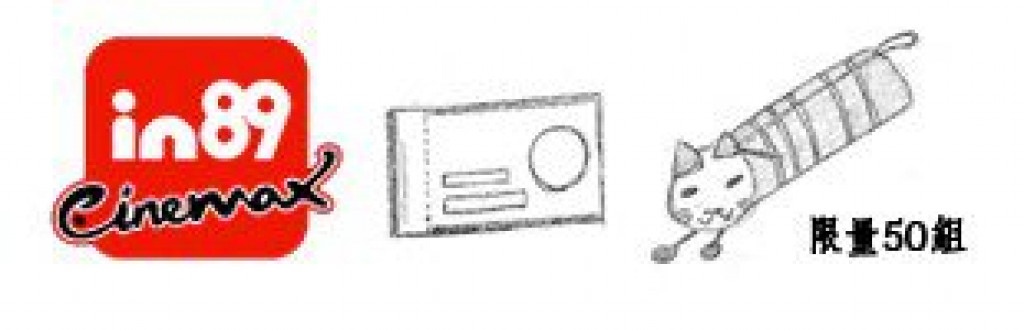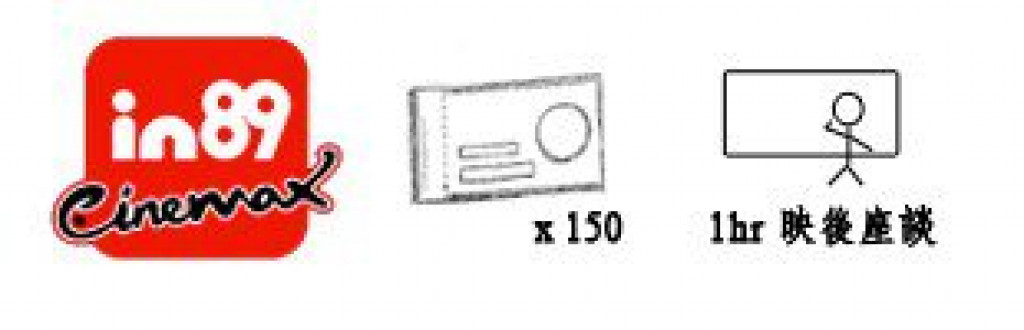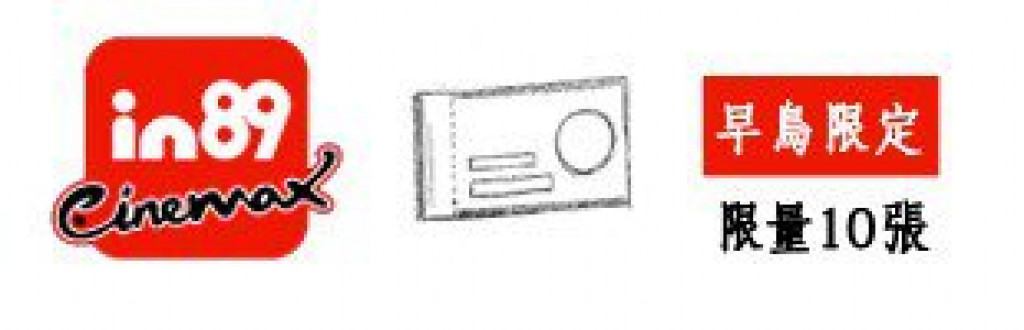感謝flyingV採訪報導
如果每個人都是世界的微光, 那我能不能把自己照亮
「我想讓我的孩子知道,聖誕節不一定會下雪,有些地方正是衝浪的季節;世界不是只有去過的美國、日本,還有很多很多值得被探索的地方。」《微光時代》以紀錄片形式,花三年記載了數名國際志工的生命故事,從印度到尼泊爾,從12歲到65歲,編織這個出走的旅程,盼望著每個人努力攀爬心裡的那座高山,追尋屬於自己不平凡的夢。
根被拔掉的生活,重新開始認識自己
將近十小時的飛行,降落在尼泊爾第二大城波卡拉(Pokhara)的阿克蘭山上,兜兜是《微光時代》裡的志工,任教於「照亮生命英語小學」,一所偏鄉學校。最初與短期志工一同抵達,但其他人服務時間到先回台灣,只剩她待完一年。服務隊離開那天,面對熟悉的人瞬間抽離,她無語地呆在一旁崩潰大哭,好像一走就剩自己甚麼都沒了。去尼泊爾後有很多在台灣習以為常的事要煩惱,像是找水找電,甚至沒有當地人幫忙時,會遇到很多生活的困難。

《微光時代》導演劉建偉分享三年來拍攝剪輯心得。〈圖/黃怡禎 攝〉
國際志工在台灣一直是個被熱烈討論的議題,面對國內與國際志工的差別,劉建偉導演〈偉導〉從服務的動機與心態來看,發現其中差異:都會區的孩子到偏鄉服務,仍容易認為自己是個「有資源的人」,那一點點驕傲可能會難以調整服務的心態。「在尼泊爾你是整個根被拔掉的,當你到一個地方,卻一無所有時,那種感覺才能真正的成長。」從台北到台東服務,台北人的身份仍然被大家記在腦中,但去尼泊爾後沒有人會在意你從哪裡來,就是個台灣人、甚至是外國人而已。不評論國內外志工的本質,而是親身體會生活的情境,到了那裡,所有背景、心中的驕傲,都要重頭開始。
阿克蘭山上沒有水和網路,每天都必須為生活作打算,提水的路程有一小時之遠,有時候懶惰不想做,可是不提就沒水喝了。在尼泊爾生活最常想的是接下來要怎麼辦,親身觸碰這些事,才會發現當我們以旁觀者角度看待事情,所有想法只是想像,在一年實踐過程中看見自己的限制,並且慢慢承認、挑戰它,「如果不突破永遠是想像,在過程中更認識自己了。」

兜兜在尼泊爾第二大城波卡拉進行為期一年的定點服務。〈圖/微光時代提供〉
紀錄片不是讓你看見別人,因為我們就活在故事裡面
2005年奧斯卡紀錄長片得主《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》教導住在加爾各答的孩子,用影像帶出紅燈區的故事。《微光時代》以紀錄片形式記錄國際志工在海外的生活,但與其說是記錄,不如說是讓志工們訴說自己的故事。在《微光時代》中,70% 的畫面沒有導演的參與,而是訓練當地的志工拍攝,這是一個新的想法,也是偉導一開始遇到的瓶頸。
「當我第一次去尼泊爾的時候,我發現我是『進不去的』,一個好的紀錄片要能夠貼近被攝者。」紀錄片的困難在於,你要如何在短時間內取得被攝者的信任,並且從中整理出脈絡,偉導笑著說:「可是我是一個大叔,也沒有足夠金錢時間待在那裡,我要拍這樣的主題是不容易的,只會像大叔在看小孩的視角。」
《微光時代》有一個很核心的點,是讓青年看到自己青年的故事。拍攝期中有很長時間在訓練海外志工影像敘事的技巧,兜兜也是其中一個被訓練的對象。尼泊爾大地震甫過,兜兜拍下與當地人一起修路的過程,志工們也會互相幫彼此記錄上課的情況,與孩童的玩耍的畫面,甚至是家庭訪問的過程,在鏡頭裡當地人是非常自在的,「因為她們就是活在那個裡面的人,而不只是去拍攝的人。」
攝影機是自己的視角,與不斷的自我對話
有次為了幫影片錄音,兜兜花了一整天在尼泊爾找安靜的地方。「那裡的喇叭聲都很吵,又有很多奇怪音調。」生動地模仿車水馬龍,為了等一切安靜竟等到凌晨兩點:「原本以為晚上夠安靜了,大雨嘩啦打在鐵皮上,終於我把自己裹在棉被裡要錄音時,昆蟲們飛過來:吱!」拍攝的過程有很多有趣的事,小朋友會搶走相機去拍牛屁股,她也會思考自己和孩子們拍攝的角度有哪裡不同。學會拍片後,兜兜發現以前為自己留下的影像很少,每天花很多時間處理生活上的難題,也沒有想過要記錄。
「我對影像是很陌生的。」認識偉導後透過拍攝,她發現這是在用更深沉的方式去記述生活,「因為這永遠不是喀擦兩下就沒了,你必須站在當下去記錄,感受當時的氛圍和情境。」放下拍攝者角色,用心體會畫面中的生活,也因此尼泊爾大地震後,趕到當地的兜兜馬上收起相機,覺得那時候不可以拍,「跟他們關係很近的時候,我反而拿不起相機。」
影像記錄工作讓她開始跟自己對話,透過相機,彷彿觀景窗就是一個台灣視角的自己,陪伴著前行觀看世界。

志工與當地居民一同生活 〈圖/微光時代提供〉
攝影機是一個與人溝通的橋梁,在印度服務一年,也遇過許多短期志工加入,在這裡發現彼此心態上的差異。「短期服務我會思考,我是來服務還只是想為我的人生留下甚麼,所以短期志工比較常拿起相機到處拍照。」偉導在訓練志工拍攝的過程也發現,待三天和一個月拍出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,「我看到一個月後的影像,她就住在當地了,真的很奇妙。」特別的是,常常覺得攝影機已經在裡面,彷彿也參與了這樣的生活。
不是眾人期待的樣子,卻是生命故事的轉變
尼泊爾很遠,卻十分令人享受,不用再害怕其他人眼光。出發前她大四,也曾幫自己想好未來人生:很棒的學歷、工作,交一個很好的男朋友,之後結婚共組家庭。「沒了!然後呢?或許這就是我所期待的人生,但好像不是我,那是別人標榜的安穩。有天如果突然發現,當你所希望的根本不是你自己的時候,那怎麼辦?」
因為一切都在摸索,甫至尼泊爾時非常保護自己,還在想像要用甚麼樣貌對待這裡的人事物,也不曉得將來會變得怎麼樣,服務隊先行離開曾使她無助,直到現在還能想起突然只剩一個人時的情景。一年的長期服務,需要跟當地人建立關係,「並不只是我認識你就好,也要讓你認識我。」在那裡學習如何和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產生連結,在那裡遇見喜歡和不喜歡的人,打破曾以為自己喜歡世上每個事物的想像。「那時我22歲,第一次這麼誠實面對自己的感覺,而在那裡,不論喜歡或不喜歡,我都要盡力去相處。」
服務當中有很多不美好的事,有次在慶典中,當地婦女伸手向兜兜要雞肉,那個對志工物質需求的依賴令她十分生氣,也失望自己能給的為甚麼這麼少。真正的助人絕對不會是熱血快樂,放入感情時難以將眼前的所見所聞與自己隔離,同樣也會有許多移情,「去到海外服務,你可能在他們身上想起很多身邊的人,你就會全部都給出去,忘記你是誰。」但在服務的過程,服務,不是把自己全部都丟進去,在過程中需要有很多界線,要知道並且記得你是誰、能做到哪裡。
「經歷了一段時間後,我才開始願意承認,去尼泊爾有一部分是為了逃。」升學、畢業,面對即將進入大人的世界感到焦慮,害怕長大之後不能作自己。然而到了之後兜兜發現,這正是能好好跟自己相處的時候、是難能可貴的機會,有很多沒想過的衝擊,也是沒有人走過的路。回台灣後,看見和自己同時畢業的朋友,有工作、在念書、甚至已經結婚了。「那個衝擊是很大的,很多人覺得作國際志工很酷,但回來我還是必須面對很多現實。」偉導在旁開玩笑說,你這樣講不公平,以前當兵還不是當兩年,回來腦袋都空了!
笑聲背後,他們心理都知道,這絕對不只是一個時間的遞進,而是生命故事的轉變。
即使漫漫長夜,我們的盼望永不止息
談論了那麼多國際志工與服務的話題,當問起拍《微光時代》的目的,原先口沫橫飛的偉導話鋒一轉,眼神堅定、語氣沉著地緩緩說道:「很單純,這就是部爸爸想拍給小孩的片,我只是想讓我的孩子長大後可以看。」每個青年面對未來的迷惘,難以安於現在的生活,不知道自己要甚麼。並這不等於必須停止追尋,「我想跟我的小孩說,你必須愛你的敵人,你可以多一點勇氣。」
作為四五十歲的中年人,最盼望地就是現在的孩子們能擁有更多體會。希望再過二十年,這些社會中堅、統治世界的人是有愛心、視野的,「我不希望大家一直想著:我們真的要逃離鬼島嗎?」去看過外面的土地,拾起勇氣放開眼光,才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。偉導看著我說:「如果你以後掌握了我的社會福利,我會希望你已經是看過世界後,才回來思考、規劃的。」語畢我以為他在開玩笑,卻發現這是多麼深切沉穩的寄託。
故事有開始、過程,但最後並不是結局,而是一個轉換。從尼泊爾回來的兜兜訴說著過往經驗,也覺得這只是個逗號:「我自己都還在路上。」而動機來自於開始,目的往往是最後。不用害怕路的終點,只要堅定地,在路上,走出屬於我們最勇敢的進行式。
電影《怪物的孩子》中,九太面對想逃避的癥結點,常會陷入兩難或迷失的漩渦,和兒時的我們一樣懷疑長大。偉導回憶在尼泊爾遇見的12歲志工,擔憂自己看不到未來,不知道以後要怎麼辦,每天放學回家與電動、電視為伍,學校教的不知道喜不喜歡但都要念完。而我們的童年何嘗不是如此?人生階段中不斷擔心與迷惘,試圖尋找出口,「我12歲的時候也想過這個問題耶!可是沒人回答我。」拍攝《微光時代》,並不是想給任何人答案,而是創造一個能跨出去的動機。「你永遠不要忘記你還有勇氣。」不管怎麼樣世界都會定義你,這就是框架,我們要去把他甩掉。
報導來源:vstory